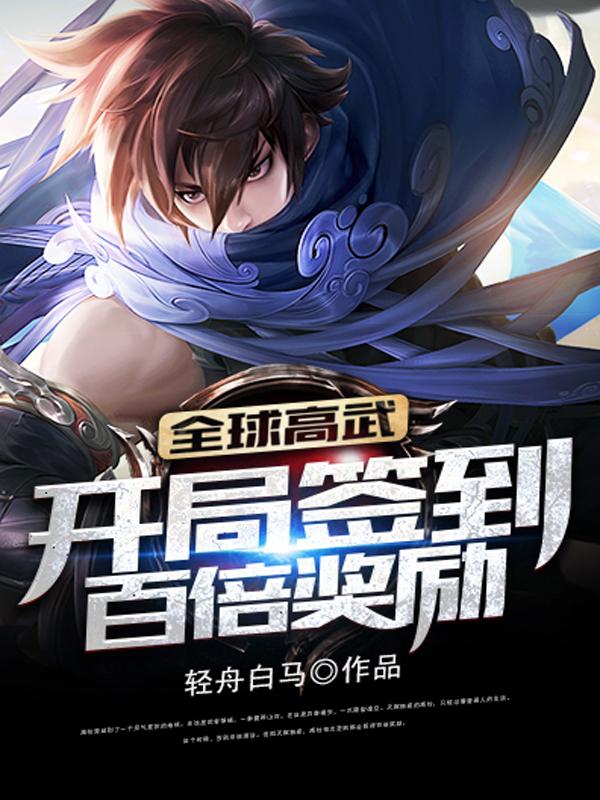第八小说>都说中医是垃圾?我靠系统出手封神 > 第178章 创新教学 沉浸式临床与古籍新解(第1页)
第178章 创新教学 沉浸式临床与古籍新解(第1页)
他指了指老先生略显苍白的脸色和淡白的舌苔。“你们看他的气色,典型的‘阳虚’之象。肺开窍于鼻,鼻炎是‘标’。但肺气的强弱,根源于脾肾之阳。脾阳不足,运化水湿无力,水湿上泛,就成了清鼻涕。肾阳不足,卫气不固,身体的‘藩篱’就弱了,所以一遇到风寒、花粉这些‘外邪’,就守不住门户,喷嚏连连。所以,他的病根,在‘脾肾阳虚’。”方铭在旁边听得心潮澎湃。这套逻辑,完全颠覆了他对疾病的认知。西医是头痛医头,脚痛医脚。而中医,是通过局部的症状,去寻找整体失衡的根源。“所以,治疗的思路,不是去‘抗过敏’,而是要去‘温补脾肾,扶阳固表’。”周翊聪开出了方子:附子、干姜、肉桂,温肾阳;党参、白术、茯苓,健脾气;再加黄芪、防风,固护卫表。“你们看,整个方子里,没有一味药是直接作用于鼻子的。但只要把他身体里的‘阳气’这团火重新点旺了,他自身的抵抗力强了,那点所谓的‘过敏原’,自然就奈何不了他了。这叫‘正气存内,邪不可干’。”一堂活生生的临床课,比读十年书本都有用。学生们如痴如醉,感觉一扇新世界的大门,在面前缓缓打开。晚上的课,更具特色。地点在道长清虚子的静室里,点的不是电灯,而是几盏昏黄的油灯。学生们盘腿而坐,周围弥漫着淡淡的檀香。周翊聪讲的,是《黄帝内经》的开篇,《上古天真论》。“‘上古之人,其知道者,法于阴阳,和于术数,食饮有节,起居有常,不妄作劳,故能形与神俱,而尽终其天年,度百岁乃去。’”他没有像大学教授那样,逐字逐句地翻译解释。而是用一种讲故事的口吻,结合现代人的生活方式,进行全新的阐释。“‘法于阴阳’是什么?不是让你们去算命。是告诉你们,要顺应自然的节律。太阳升起,你就该起床,阳气升发。月亮出来了,你就该休息,阴气内敛。现在的人,天天熬夜,晚上十一二点,本该是胆经肝经排毒、阴气收藏的时候,你还在刷手机、打游戏,人为地消耗阳气,扰乱阴阳。这叫‘逆天而行’,身体能好吗?”“‘和于术数’又是什么?‘术’,是方法,是导引、吐纳、针灸。‘数’,是节律,是度。吃饭要七分饱,是度。运动要适量,过犹不及,也是度。中医治病,用药讲究君臣佐使,讲究剂量,更是对‘数’的精准把握。所以,中医是最讲‘科学’的,只不过,它的科学,是关于‘度’的艺术,而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。”他结合系统赋予的【黄帝内经·完整版】的深层理解,将那些古老而晦涩的文字,化作了学生们能听懂、能感受、能实践的生活智慧。方铭听得入了神。他想起了自己为了写论文,通宵达旦地查资料、做实验,把咖啡当水喝。他以为那是勤奋,是上进。现在想来,那不过是在用最愚蠢的方式,透支着自己最宝贵的“先天之精”。一堂课下来,学生们没有丝毫疲惫,反而觉得神清气明,心中充满了宁静与希望。深夜,学生宿舍里,灯火通明。一群年轻人围坐在一起,兴奋地讨论着白天的所学。“太神奇了!我今天才知道,我奶奶常给我吃的‘车前草’,居然是利尿通淋的良药!”“周校长的临床思路太强了!简直是降维打击!我感觉我以前在大学里学的都是假的。”方铭没有说话,他正在自己的笔记本上,飞快地记录着今天的感悟。他写下了今天课程的标题:《第一天:世界观的重塑》。他知道,这仅仅是一个开始。在这里,他将要学习的,不仅仅是医术,更是一种全新的、看待世界和生命的方式。远处,周翊聪的房间里,灯也亮着。他没有休息,而是摊开了一张巨大的图纸,上面画着的,正是那两份合二为一的【聚灵阵·残图】。广南之行,让他深刻地意识到,要对抗庞大的资本和根深蒂固的偏见,光靠医术是不够的。他需要更强大的力量。而这聚灵阵,或许就是那把能够撬动整个格局的,关键钥匙。他端起保温杯,呷了一口温热的茶水,目光深邃。窗外,星河璀璨。中医传承的星星之火,已经点燃。而他,将要为这团火,添上一阵足以燎原的,东风。神州国医大学的第一个秋天,是伴随着药香和书声度过的。清晨,学生们跟着道长在百草园里吐纳导引,感受着草木间的勃勃生机。上午,他们或在田间地头,跟着老药农辨识药材,亲手触摸那些在书本上只是一个个枯燥名字的生命;或在诊室里,观摩周翊聪如何通过细微的脉象和气色,洞悉患者身体里的惊涛骇浪。下午,是古籍新解,周翊聪用最生动的方式,将《黄帝内经》里那些玄奥的智慧,揉碎了、掰开了,讲得通俗易懂,直指人心。小主,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,,后面更精彩!方铭的变化是最大的。他剪掉了精心打理的发型,换上了和大家一样的棉麻布衣,曾经那份属于天之骄子的锐利和优越感,被一种沉静的求知欲所取代。他不再迷信于冰冷的仪器和数据,而是开始学着用自己的身体去感受,用自己的心去思考。他会为了一个穴位的准确位置,和同学争论到面红耳赤;也会为了搞懂一味药的“偏性”,在药圃里蹲上一整个下午。基地里的一切,都充满了希望,仿佛一棵古老的树,正在发出嫩绿的新芽。然而,这片宁静很快就被打破了。风暴,起于大洋彼岸。起初,只是一些不起眼的浪花。几家国外的健康类媒体,开始刊登一些所谓的“专家评论”,文章的标题充满了偏见与傲慢——《草药的狂欢:东方神秘主义对现代医学的冲击》、《“清瘟败毒饮”背后,是科学的缺失还是标准的空白?》。这些文章引经据典,用大量看似“科学”的术语,将中医的成功归结为安慰剂效应,将周翊聪的公开药方,描绘成一种不负责任的、可能引发未知风险的“巫术”。在国内,这些论调很快被民众的口水淹没。开玩笑,广南省上千万人的亲身经历,是你们几篇文章就能抹黑的?“洋大人不懂就别瞎逼逼”、“建议专家来广南的icu住几天再说话”,类似的评论在网络上随处可见。:()都说中医是垃圾?我靠系统出手封神